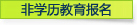專家建議對宅基地管理統一立法
來 源:法制日報發表日期:2012-11-13
北京市農村法治研究會一項針對宅基地政策的專題調研報告近日披露,調研發現,與宅基地有關的法律與法律、法律與政策之間的沖突性規定大量存在。包括土地征拆遷等一系列與宅基地相關的規定,可謂千差萬別。
為了維護農民住房權益和法制統一,調研報告建議制定《農村宅基地及農民住宅法》。
這份報告的全稱為《〈北京市農村宅基地及農民住宅條例〉法規預案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該專題報告已收入《北京法治發展報告(2011)》。
各地規定五花八門
報告稱,對于超標占地的情形,各地有不同處置原則。昆明市要求村民“騰退超標準占用的宅基地”;廈門市實行“宅基地有償使用制度”,并鼓勵村(居)民委員會組織公開招標;山東省和德州市均通過宅田掛鉤方式相應扣減村民的承包地面積,德州市還進一步規定“由村集體與申請人簽訂承包協議,臨時確定給申請人發展庭院經濟”。
對于村民因繼承而取得的多戶住宅的處置方式,各地規定也不一樣。河北省規定必須將多余的住宅轉讓給符合宅基地申請條件的村民;三亞市和海口市規定,要求村民將多余的宅基地退回并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安排使用;上海市、黃岡市和株洲市則規定,可以確立這些宅基地的使用權;山東省菏澤市則對此區別規定,對于符合申請宅基地條件的,可以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對于不符合申請宅基地條件的,注銷其土地使用證或用地批準文件,由村民委員會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回宅基地使用權。
對于近些年廣受關注的集中建房問題,上海市規定由區(縣)人民政府組織制定集體建房實施計劃,由村民委員會負責具體實施;福建省規定了集中建房包括統規統建、統規自建、統一舊村改造等方式,實施主體則可以是鎮鄉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員會。
法規和法規之間沖突
報告稱,各種規定之間的沖突造成實踐操作中的混亂局面,增加了相關部門的執法難度。
最引人關注的不同規定,莫過于在城鎮居民能否購置宅基地的問題上。于1993年頒布實施的《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回原籍村莊、集鎮落戶的職工、退伍軍人和離休、退休干部以及回鄉定居的華僑、港澳臺同胞等城鎮非農業戶口居民等特定人群,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權主體。
而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明確禁止“城鄉居民占用農民集體土地建住宅”,2004年11月國土資源部《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再次強調“嚴禁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
法律和法律之間“撞車”
除了法律與政策規定不一,法律與法律之間也有沖突之處。如對“違法建設”的治理上,城鄉規劃法和土地管理法分別規定了兩個不同的執法主體。城鄉規劃法規定“由鄉、鎮人民政府責令停止建設、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后者則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退還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由于管理主體規定不一,實踐中常常出現鄉政府和國土管理部門相互推諉甚至扯皮的現象,政府執法權威性和公信力受到極大削弱。
同一部門規章之間“打架”
就連同一部門規章之間,也因缺乏連續性產生沖突。國土資源部2004年的《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指出,“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面積不得超過省(區、市)規定的標準”,強調“一戶一宅”;2008年的《關于進一步加快宅基地使用權登記發證工作的通知》又規定“除繼承外,農村村民一戶申請第二宗宅基地使用權登記的,不予受理”,隱含著“合法繼承的宅基地可以予以登記”的意思。
省級地方性法規缺位
之所以各地規定呈現差異,報告指出,與針對農村宅基地尚無一個清晰的制度框架、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缺位密切相關。
報告指出,目前與農村宅基地及其住宅有關的法律主要包括土地管理法、物權法和城鄉規劃法等,但其內容過于簡單,缺乏體系性設計。
課題研究者以“宅基地”為關鍵詞命名的市級以上規范性文件中,省級規范性文件有7個,地市級規范性文件有33個。在這40個規范性文件中,省、市政府頒發的主要為33個,國土資源廳發布的有1個,以市政府辦公室名義發布的有6個。這些文件主要圍繞宅基地的申請條件、程序、面積標準及違規用地的法律責任等作出規定。
目前,尚無一個由人大出臺的省級地方性立法文件。山東省人大常委會曾于上世紀80年代初制定過《關于農村建房占用土地問題的決議》,但內容簡單時效性差,對現實參考意義不大。
也正是由于全國層面的法律調整不足,地方人大規范缺位,大多數具體事項都由利益相關方的政府出臺文件進行調整,報告認為,這難免給法制統一帶來挑戰。
建議制定農民住宅法
報告認為,根據現有國情,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城鄉住房一體化管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民住房仍將依賴于宅基地。這使得農民住房管理制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專門立法。就此,報告建議參考《農村土地承包法》,出臺全國統一的《農村宅基地及農民住宅法》。

 關注學院官方微信
關注學院官方微信